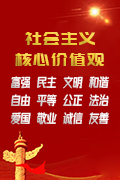身边好人
您的位置:首页 >>身边好人2018-08-24
安徽砀山71岁老人汪正英为了兑现自己的承诺,他坚持拾荒13年,终在前几日还清了50多万元的债务。如今一生的夙愿终于完成,汪正英也深深松了口气,他说,“还债的压力让我连父母去世都没能回去,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带着儿孙回老家砀山,弥补一生的遗憾。”
1943年出生的汪正英,老家住在砀山县周寨镇汪蒋庄村。1965年,22岁的汪正英远赴新疆阿克苏市工作,在公路管理局工程处修桥修路,并在当地娶妻安家。随着两个儿子的相继出生,四口之家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。1993年,汪正英提前办理退休手续后,开始承包筑路修桥工程。经过几年的努力,汪正英手下有了30余名工人,事业逐渐有了起色。“那时候每年收入都不错,家里的日子越来越好了。”回忆起当年的幸福时光,汪正英唏嘘不已。
天有不测风云,不幸的事接二连三发生。1998年,汪正英先是在一次施工送货途中发生严重交通事故,导致腿部粉碎性骨折,不久又遇到建筑单位拖欠工程款。两次事故让他花光了家里的积蓄,还欠下了50多万元外债。因为无法支付工人工资,原本富裕的生活变得捉襟见肘。
妻子无法接受生活的剧变,选择与他离婚。他把房子留给妻子,一无所有、带着巨额欠债的他到乡下租住了一间小屋。“那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为黑暗的记忆,每天都在煎熬中度过。”往事不堪回首,汪正英说,“但人再穷也要有骨气,我欠的钱我就要还清,我坚信,在我有生之年,一定能还完这些债务。1998年至2002年间,汪正英带着工人去各地要钱,仅追回了部分欠款。之后,工人、材料供货商纷纷上门讨要欠款。汪正英向他们打下欠条保证说:“相信我,不管到什么时候,钱我都会还。
虽然每个月有3000多元的退休金,但对于50多万元债务来说,简直是杯水车薪。“如果光靠这些退休金来还债,每个月一分钱不花,至少需要15年才能还清!所以我必须想其他途径多挣钱,可自己年纪大了,身体又不好,到哪找挣钱的门路啊?”汪正英说。无奈之下,汪正英开始拾起了荒。2002年起,他没日没夜地穿行在阿克苏市的大街小巷、商店、饭馆,捡拾各类废品垃圾,每天只睡5个多小时,并规定自己每天必须捡够5大袋的数量。“夏天还好,冬天就不行了,新疆这边冬天气温都在零下20多度,捡废品以来,我的两只手就一直皲裂,从来没好过。”老人说。不过,每天都有卖废品的收入,老人的心里略显满足:“辛苦是辛苦,但一公斤废纸能卖5毛5,一公斤饮料瓶能卖两块八,每个月靠捡垃圾能多挣1000多块钱呢!也许,这是我能早日还清债务的唯一途径了。
汪正英每个月留下300元当生活费,其他的钱加上退休金,一到月底攒够一定的数量,就主动联系债主把欠款还上。时间一长,原先催债的工人不再催他还钱,有人甚至和他成为了朋友。虽然很累,但每天想着债务越来越少了,我就越干越有劲。”汪正英乐观地说,“我把拾荒当成锻炼身体的方式,别看我70多岁了,但身体好、有力气,一袋200多斤的废品,我一下子就能搬到车上。汪正英的两个儿子在新疆都有了工作,他们也曾多次劝说父亲,欠下的钱一起还,可汪正英坚决不同意。“债是我欠的,就要我来还,与儿子们无关,不能给他们的家庭增添负担。再说,他们的生活压力也不小,不能因为欠债的事情重蹈我的覆辙。”汪正英说,“我在乡下租住的小屋里堆满了废品,10多年来,我从不让儿子到这儿来,有事我就和他们约在城里见,就是怕他们为我担心,影响他们工作。
说起拾荒十来年里最大的遗憾,汪正英感到非常愧对自己的父母。他说:“我很感激我的父母,他们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村人,都支持我拾荒还债。我想我骨子里继承了他们的坚强和诚信。十多年来,我从未回老家尽过孝,也没有给父母寄过钱,可父母从不生我的气,只希望我能早日还清债务,做一个有信用的人。为了还债,2010年和2013年,父母在老家砀山相继去世,我没能回去,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。
靠着每个月的退休工资和拾荒的钱,2014年,汪正英老人基本还清了债务,只差最后一笔没有还清。今年1月4日,72岁的汪正英又攒够了8000元现金,准备还给最后一位债主—10多年前在兵站卖土特产的康先生。但是由于康先生搬了家,汪正英怎么也找不到他的下落。为了还债,百般无奈的汪正英找到阿克苏日报社,希望在报纸上刊登“寻人启事”,寻找债主康先生。在多家媒体的帮助下,他终于联系上了康先生。康先生了解到汪正英的情况后,觉得老人年纪大了,生活很不容易,便决定不要欠款,但汪正英说:“这不是我的钱,我坚决不能要,既然康先生发善心,不要欠款,那就通过媒体,把这笔钱捐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吧。
汪正英老人的事迹曝光后,感动了整个阿克苏市,许多市民都被他的诚信所打动,钦佩老人的执着和守诺,称他是“诚信的老爷子”。对于大家的赞誉,汪正英谦虚地表示:“不管欠人家多少钱,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。人这一辈子,穷不能赖,富不能坏,做人不能没有良心,要讲信用。我要趁着现在身体好,多做善事,做一个有尊严和声誉的人。(百家号)
责任编辑:赵彧喆